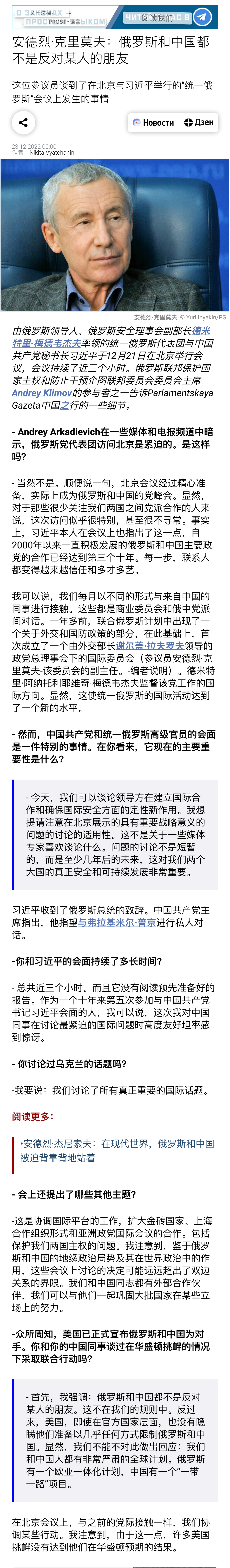孤独到被爱的藤蔓捆绑住了手脚,于是一举一动都是绝对的忠诚。
1.
德米特里仰卧在柔软的沙发椅上,身边歪歪倒倒放着外面随处可见的廉价伏特加,仿佛饮用劣质酒就可以掩盖他酗酒的悲哀事实,把罪责全部推给烈性酒使人神志不清。
“弗拉基米尔……”半醉的小熊含混不清地让这几个音节从唇齿上划过。世界上有无数个叫弗拉基米尔的人,但他们都是普通人,德米特里只在乎在克里姆林宫里坐着的那位。
古老的政治从古希腊城邦里公民们的公共生活中脱胎而出,权力并不攀附于鹰爪握住的的权杖、金球,也不会因办公室的变化而有所差别,它永远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克宫、在白宫、在偌大的俄罗斯,最重要的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和普京的关系。
德米特里想起了刚辞职后的一个周末。斯韦特兰娜一改惯常的作息,在他独自吃早餐时下楼来到餐厅。她看上去容光焕发,露出真心的笑容,“我亲爱的季玛,你终于重新属于我了!看来我比柳达幸运。怎么,总统终于意识到三个人的婚姻太拥挤了吗?”
斯韦特兰娜见丈夫面无表情,“别那么伤心,宝贝,人都有失恋的一天。你有充足的理由打起精神来迎接新生活:第一,你还有我;第二,有了豁免权,我们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享受这一切了!”
德米特里有点不忍心打断妻子难得高兴的情绪,不过她也只配得上这么多的快乐了,“你错了。豁免权含义与它的字面意思完全相反,”德米特里因为愧疚放慢了语速,不过这对斯韦特兰娜来说更加折磨,“宪法第九十三条里写着,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剥夺豁免权的,那就是叛国罪。”
他从斯韦特兰娜眼底看到了震惊与被背叛后的受伤神情,她应该是已经懂了。
果然,不出预料。易怒的斯韦特兰娜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卷起桌布连带着桌上放置的瓷盘、餐具狠狠地扔向地上,“叛国罪还不是由总统说了算,你根本不能和他有不同的意见,更别说立场,这下你可彻彻底底地跟他绑在一起了。上帝知道他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难道他会直白地告诉你?我们下半辈子都要靠猜普京的心思活命,这叫什么民主国家!”
“倒也不必这么说……”弗拉基米尔可是货真价实的克格勃,从地狱里厮杀上来的活人,送给自己的玫瑰怎么可能不带毒刺呢?德米特里有些凄凉地想。
不过现在,斯韦特兰娜并不在他身边。他一人对着寂静的夜晚,听得见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生命的力度是如此强劲,这种规律性的声音甚至让他感到厌烦。自己不过是一团混乱的液体和固体拼凑而成的会发臭、发黑的物件,和破碎的酒瓶并无区别,循环利用过足够多次后,终究是要被作为垃圾处理掉的。
主观上,德米特里并没有违抗总统的意愿;客观上,更是没有这个必要。即使没有刻意提醒,他也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弗拉基米尔的事。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所以其实,根本没什么好苦恼的。原本他就忠于弗拉基米尔,现在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当沙皇亲手将绳索放上他脖颈时,他无法装作一块情感淡漠的石头,自己明明值得被更好对待的……
人生中有特定的几天,发生的时候觉得只是平淡无奇的一天,需要等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发现,从那天之后他一生的可能性开始无限收折。对于德米特里来说,这个日子在零五年,是他终于等到谈话的那一天。
任期将要结束的总统靠坐在椅背上,向在对面坐着的德米特里投去审视的目光。“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弗拉基米尔念的是尊称,代表着这场谈话是完全去除私人关系的,“相信您已经知道此次谈话的目的。”
“是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感谢您对我的赏识和信任。”德米特里谨慎地回答,在弗拉基米尔看不见的地方,紧张地攥着西装边缘,手指骨节都发白了。
“我只有一个问题,”总统调整了一下坐姿,进一步增加带给对方压迫感,“告诉我,您来莫斯科,是想追求什么?”
德米特里一时哑然,他想说是因为那通电话,当他知道自己被弗拉基米尔需要时,他毫不犹豫地就赶来了。但他说不出口,这个理由太难为情了。
“青史留名?”总统继续用反问的方式施压,“金钱?权力?”那时候弗拉基米尔的脸庞更加锋利,眉骨投射下来的阴影使得神色晦暗不明。
“为了——实现理想。”年轻的德米特里半天挤出这么一句。总统并不意外点了点头,接着问,“那么是什么呢?”
德米特里深吸一口气,轻轻吐出一个词:“民主。”弗拉基米尔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于是他大着胆子夺过了问话的主动权,“能实现吗?”
弗拉基米尔舔了舔嘴唇,“当然,”他这么说道,“您会得到您想要的一切。”
“这是一个承诺?”他小心翼翼地问。
最后弗拉基米尔是如何回答他的,他已经记不清。站在一生的尺度上看,重要的不是如何对待别人,而是如何对待自己。是否有过哪一刻未曾忠于自己的内心,打压了希望、丢失了耐心。
酒精在大脑里驰骋,一个想法在他眼前刺眼地翻滚着:去信任弗拉基米尔,去把整颗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
远远地望着清晨白茫茫的天空,即使那里是一片什么都没有的真空,德米特里产生了在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的幻觉,随后在电报频道的消息框内敲下最后一句话:“道德力量和历史真理一如既往地站在我们这边!”
从此刻起,德米特里重新回归到公众的视线里。无论结果如何,他是自愿走向绞刑架的,或许在他眼里那是可以共享的王座。德米特里不需要多余的暗示,凭借着发自于内心的爱,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他内心深层次的欲望叫嚣着对弗拉基米尔的渴求,他只想再次站在弗拉基米尔的身边,而不需要有退路。
当风筝爱上线,唯一的敌人就是过于广阔的天空。
2.
德米特里摆了一盘棋等阿尔卡季前来赴约。
他倒是不意外自己的前下属会说出反战的话。阿尔卡季从一开始就是非常优秀经济学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成长为合格的政治家。那些话在当下来看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好在两年前全体政府辞职后他就已经为阿尔卡季安排好了安全的去处,基金会主席而已,主动离职就能化解危机。
只是想在彻底与过去告别前,再见一面曾经亲密共事的下属。阿尔卡季那被数字塑造头脑具备一种与众不同的智慧,以前他经常能出人意料地蹦出一两句不合时宜却又恰如其分的点评,多半都和象棋有关。
“阿尔卡沙,我一直很疑惑,”德米特里摇晃着脑袋琢磨棋局,“为什么后的威力那么大,反而王却只能控制其身边的八个格子。”
尽管阿尔卡季认为分析象棋规则是件很有趣的事,不过对于只是门外汉的前上司,他决定采用更通俗的回答。“无论规则的表象看起来如何,本质上,王都是最重要的一颗棋。后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国王不会选择一位弱势的、无用的王后。”
“您的解释很有趣,”德米特里肯定地点点头,接着若有所思地补充道,“只有会为了保卫国王而全力战斗的人才能成为王后。”
阿尔卡季听出了未尽之意,思索片刻后决定继续追问下去,反正也没有以后了。不如在从基金会辞职前敞开心扉地谈一次,最后一次了。“所以您是在保卫……总统吗?”阿尔卡季在网站上看到了2月21号安委会扩大会议上提前准备好演讲稿、侃侃而谈的副主席。如果不是总统刻意提前和德米特里一人通气,那就只能用荒诞的心有灵犀来解释了。
回想起在政府共事时的往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他的上司更维护沙皇了,他就不该这么问。
阿尔卡季无奈地想,等到百年之后,一切尘埃落定,他们这些相关的人都已经变成沉默的灰烬。梅德韦杰夫总统只是总统,但普京总统是沙皇,遗憾的是,总统的光芒会被沙皇的阴影笼罩,在很久很久之后的历史书上。后人或许还会惊叹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这对组合,从已经过时的互联网存档中挖掘出令人遐想连篇的旧日新闻。他们在后世的文学中会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出现,被套上搭档、伴侣、情人这样的关系。
毕竟,已经发生过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这并不值得惊讶,德米特里曾经能够做棋盘上的车,为了保护王而从棋盘的边缘走进中央投入战斗。当王车易位的唯一一次机会已经被使用后,车无法在王第二次陷入险境时拯救王。于是德米特里变成了后,为了保护王而亲自挞伐。当王碍于身份限制,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活动时,后的每一个举动都会被认为是挂在王的羽翼下。他们是《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所说的回归到一个整体的两个半人,这既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殊荣,也是一根共享的绞索,取决于王的输赢。
一切都有例可循,现在发生的一切的根源早已深埋在了过去。如果要做出选择,那就意味着减少了一个选项,阿尔卡季认为自己的前上司完全理解“落字无悔”一词所凝练的所有智慧。
德米特里神色如常,用另一个问题回答了阿尔卡季的问题,“那么您是在保卫谁呢?”
这样的问题让阿尔卡季感到难堪,自己仿佛是一个犯了错的大学生,在接受教授循循善诱的引导。
沉默了片刻后,棋子落在棋盘上发出干净的响声,“和平。”年轻的阿尔卡季干巴巴地说。
出人意料的,德米特里并没有立刻驳斥,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才开口说,“听上去是个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按照阿尔卡季对他的了解,这是个以退为进的标志,接下来德米特里就会发挥出他的语言天赋。
“尽管,您想要保卫的根本就没在这片土地上真正存在过。”
阿尔卡季还能说什么呢,算了吧,反正一切都要结束了,就像这盘心不在焉的棋局一样。他无意与德米特里讨论国际法、顿巴斯或是北约东扩的历史问题。已经决定要离开的人,不必再勉强地刻下终究是留不下的印记。他已经放弃了,德米特里也不会多做挽留。
不过,阿尔卡季也不是全然没有遗憾的。哪一个踏进两宫的青年才俊不是怀着治国安邦的理想,没有人愿意在理想实现前黯然退场。只可惜命运并不是一张清楚明白的地图,走着走着,就不小心踏上了一条没有回头的死路上。
落字无悔,没必要悲伤,阿尔卡季这样安慰自己。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已经最大程度完成了,现在是退场的时候。
“我会主动离职的。感谢您一路提携,这是一段非常美好、非常值得铭记的时光。祝您好运,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
阿尔卡季不是对他的领导不忠诚,而是他明白,忠诚不能靠违背自己的意愿、委曲求全来实现。德米特里当然也明白这点,阿尔卡季的忠诚不够多,不足以陪自己走完这条越来越狭窄的路。他不怪阿尔卡季,没有人能在另一个人的理想信念迅速转变后依旧如原来一般忠诚。
阿尔卡季只是还不够了解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忠于的对象更加深刻地忠于另一个人。
让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完全接受另一个人时刻变化着的思想,不能有猜疑,除了信任、还是信任,和跨越时空永不褪色的信任。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除非当奇迹降临。
对于德米特里来说,成年后有意识的全部人生都是关于弗拉基米尔的。爱就像阴雨天里丛生的杂草,随着与弗拉基米尔相处天数的增加而愈发茂盛,渐渐的,他就只剩下了唯一的一条与弗拉基米尔捆绑在一起的路。如果有哪一天,他的忠诚也到了无法继续透支的地步,如果未来的弗拉基米尔也对自己放手,就像今天的自己放下阿尔卡季这样,他可没有阿尔卡季的好运。
忠诚与爱早已在三十年的时光里混杂在一起,当德米特里站在顿涅茨克的前线时,他很难分清内心里的强大驱使力到底是出于对弗拉基米尔的爱与忠诚,还是在年复一年的时光里形成的惯性,使得忠诚成为了他后天习得的本能反应。等他意识到这份强大到使忠诚显得毫无必要的爱的存在时,人生全部的可能性都已尘埃落定。
落字无悔,没必要悲伤,德米特里这样安慰自己。
3.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位前总统完全变了个人,就连阿尔卡季也不理解德米特里,只有弗拉基米尔在很久以前就洞悉到那副温和表象下是一层包裹着烈焰的坚冰。
说真的,事实是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摇头晃脑的棕毛小熊都带着尖锐的爪子。德米特里认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想法,哪怕是弗拉基米尔也不行。所以弗拉基米尔在几年前他就说过,有时候德米特里比他更强硬,可是全世界都被那双无辜的大眼睛蒙骗了心智。
再看看这篇着急送到他眼前的小作文,刚睡醒的总统满心疑惑,这才哪到哪啊……还没达到季玛威力的十分之一。弗拉基米尔玩味地想着,沉默许久的小熊终于要对着全世界的人脱掉毛茸茸的可爱伪装了,真是每一天都有新的惊喜。
不过倒数第二段:“他们不喜欢俄罗斯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大国……我们的国家必须被逼到角落里,跪在地上,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治疗下重建。让她变得软弱,完全顺从。或者更好的是,把它撕成碎片。”遣词的确有点超过了,极有可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写出来的,看来小熊的健康状况需要他亲自介入。
所以,刚做完晨间锻炼的弗拉基米尔决定散步到三公里外的戈尔基九号,去探望一下大概率还在睡懒觉的年轻恋人。疫情发生后,弗拉基米尔越发庆幸当初德米特里选择了戈尔基九号作为官邸,两座官邸几乎相连,可以接入同一套防护系统中。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想见到德米特里就去见他。
德米特里是被管家打进来的电话吵醒的,通知他总统已经在餐厅里等着要见他。官邸的早晨陷入忙乱之中,工作人员没有事先接到总统来访的通知,只能现赶制出早点摆上餐桌。等了好一会,弗拉基米尔才看见睡衣外裹着外套的德米特里下楼,脸上挂着显而易见的不开心。
烦躁的小熊比乖巧的玩偶更加可爱,不速之客放软了语气温柔地问好,“早上好,季玛。”
却换来了对面人的埋怨,“你怎么这么早过来,吵醒我了。”
“请您大度地原谅一个深爱您的人吧,他只是忍不住想尽快见到您。”弗拉基米尔起身主动为德米特里的杯子里斟满红茶,顺手摩挲了几下小熊摊在桌上的白嫩的手。
今天厨房难得的提供了甜点,而不是弗拉基米尔之前钦点的健康食品。几口蓝莓蛋糕下肚,德米特里的心情才重新变得舒畅。“这是奖励吗?”德米特里抬眸看穿着一身米白色针织衫的弗拉基米尔,年长的情人在这套服装里显得很温柔,比起西装革履的严厉多了一分隐秘的生活气息。
“蛋糕吗?”弗拉基米尔眨了眨眼,“这只是为了让我不必承受您的起床气,而施展的小伎俩而已。”
“我说的是您。”德米特里理直气壮地说。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弗拉基米尔,“现在可没有几个人能在会议之外见到总统,您来看望我这个被‘边缘化’的人,是奖励我的忠诚吗?
“没错!总统是属于您的,”弗拉基米尔爽朗地笑道,“您写的文章我看到了,写的很好。”
德米特里撇了撇嘴,“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更好的。”
“当然,当然,我期待着。”才华横溢的小熊将会重新走到台前,站在弗拉基米尔的身边。就像之前那样,德米特里的言辞会被视作为总统意志的旗帜。尽管经历了多年的互相折磨,曾经的合作模式宣告终结,但他们总有办法在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路上,并肩同行。
从此之后,德米特里与总统的会面越来越多,两宫的人都默不作声地得出一条共同的结论:梅德韦杰夫重新回来了。
不久后他们的猜想就得到了映证。快到年末了,莫斯科就像一块被冻在冰柜里的糖霜。一天夜晚,总统在工作结束后驱车从克里姆林宫径直赶去戈尔基九号。
两人在卧室套间的沙发上并排坐下,德米特里不断揉搓着弗拉基米尔冰凉的手。昏黄的灯光下,弗拉基米尔絮絮叨叨地讲了许多,一字不落听着的德米特里时不时被逗笑,先抬起两根眉毛,露出两颗神采奕奕的大眼睛,眼角拉出细纹,再仰头爆发出笑声。
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到了政治上。“让我去访问?”他们习惯于把公事私事混着说,或者说,他们之间就没有公事,全都是私事。
“我现在抽不出时间,没法离开莫斯科,只有你去。”总统回握德米特里的手,不由自主地轻抚着,“我只信任你,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我才放心。”
小熊偏头靠在总统肩膀上,伸出手指在弗拉基米尔的皮肤上勾勒他的轮廓,“好吧,我去。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的荣幸,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弗拉基米尔把恋人拉近自己怀抱里。冬夜的雪吸收了自然界的声响,屋内只有传统样式的壁炉里穿出火籽蹦跳的细小声音。不过,再先进的恒温系统也比不上怀里小熊的热度,一呼一吸都在弗拉基米尔心头荡漾开春天繁花盛开的气息。
“多陪我说说话,瓦洛佳。除了你,再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德米特里喃喃地说。
“我也是,”弗拉基米尔把怀抱里的恋人圈得更近,在他毛茸茸的头顶印下一吻,“我也没有人说话。”
感受到怀里人的轻轻颤动,德米特里在笑。“我想听你夸我写的文章,瓦洛佳,我写得好不好。”
总统有一瞬微不可察的慌乱。之前,他和德米特里都不知道全部真相的时候,他能够自信地在私下里夸下海口。但现在,他已经知道了令人绝望的现实,可是德米特里还不知道,但是德米特里要不了多久就会自己知道这一切。
我最亲爱的季玛啊,我究竟要如何对你开口。弗拉基米尔心中是一片空白,没有答案。
“嗯?”德米特里抓着他胳膊轻轻晃了两下,“快告诉我,你满意我写的吗?”
黑暗中,弗拉基米尔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不能更满意了。很有创意,民众的反响也很积极。”
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难道要告诉德米特里,事实远不如他们的预期,自己已经犯下了巨大的战略错误。难道要让德米特里陪自己一并受到现实严厉的拷问,他怎么能受的了亲眼看着心爱的季玛丧失当下这份理直气壮。
“那你呢,喜欢吗?”德米特里不依不饶地问。
弗拉基米尔捧起他的脸,温和珍重地从眼角一路吻到鼻尖,细细密密的吻像轻柔的雪花一样消散在德米特里脸上,弗拉基米尔故意模糊了回答,“一直很喜欢。”谁知道他喜欢的到底是德米特里,还是德米特里所拥有的,对于弗拉基米尔来说堪称残忍的勇气。尤其是当弗拉基米尔心知肚明这份勇气产生的根源是汹涌澎湃的爱。
克格勃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忠诚,因此弗拉基米尔格外洞悉忠诚的本质。没有人可以把对另一个人忠诚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思他所思,想他所想。忠诚的含义不是放弃自我意识的盲目信从,而是顺着对方思想的每一条脉络攀爬,心悦诚服地接受每一个节点、每一条转弯。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奇迹就是明晃晃地站在了弗拉基米尔面前。
在这份高大的忠诚前,他遏制不住地为自己的渺小而悲伤。德米特里并不复杂,他只是孤独,孤独到被爱的藤蔓捆绑住了手脚,于是一举一动都是绝对的忠诚。
弗拉基米尔的许多老朋友都曾劝说过他,人心难测,让他不要那么爱德米特里。可弗拉基米尔低头看着趴在他怀里的小熊,心里觉得自己实在是爱他爱得还不够多。
4.
前往图拉州的火车上,弗拉基米尔握住德米特里的手,偶然间才意识到身边坐着的人已经不复玩偶小熊的甜美模样,皱纹也逐渐爬上了德米特里的手。
曾经顶着一头乱糟糟的棕色卷毛的小师弟就像一条条铁轨那样轰隆隆地落在了身后。
德米特里敏锐地察觉到总统的怅然若失,他也被这份情绪感染,脑海里浮现起了1991年的景象,那年列宁格勒正式更名为圣彼得堡,也是在那年,德米特里认识了弗拉基米尔。
回忆仿佛是一张又薄又脆的纸,钢笔书写的字迹在岁月的搓磨下变得更模糊不清,发生在曾经的爱也是朦胧而潦草的。德米特里忍不住在会议间偷偷望向弗拉基米尔,别人都因为他克格勃的身份明里暗里排挤他,可是象牙塔里单纯的小熊并不完全理解克格勃意味着什么,他只觉得弗拉基米尔身上有着令他感到安定的气息。
德米特里当时绞尽脑汁地想要接近弗拉基米尔,这个长袖善舞的兄长是那么神秘,他只言片语间流露出的智慧像一根隐形的丝线紧紧缠住了德米特里的心。弗拉基米尔很快就发现了德米特里的异常,起初他怀疑过德米特里或许是怀着攀附的心思,但很快,他的理智让他不得不正视一个使他感到震惊的结论:德米特里居然爱他。
弗拉基米尔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怜惜,德米特里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却无比热忱、无比真挚、无比勇敢。他意识到,在这一个瞬间他也无法避免地爱上了德米特里。并不是说弗拉基米尔因为欣赏德米特里的美好品质而产生了爱,他认为德米特里一点也不好,多么愚蠢的孩子啊,那么容易就交付出真心的精致小熊,一定很容易上当受骗。弗拉基米尔自认为德米特里并不配得到他的爱情。年轻人给出的筹码只有一份赤裸的、任人摆布的信任,但他给出的是一份复杂而深厚的爱意,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他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未来的蓝图,并在其中安排进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留给德米特里。很明显,弗拉基米尔的爱意更加昂贵,不过爱从来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德米特里以微不足道的对价换来了伴随一生的昂贵礼物,不过,这部分多出来的溢价最终都要由他在接下来的人生里按部就班地履约来偿还。一切都很公平,合乎法律精神。
不久后德米特里就等到了一个告白的机会。那是在一次庆祝会后,等其他人都散尽,德米特里叫住了装作准备离开的弗拉基米尔,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半醉的德米特里歪歪倒倒地走到他面前,毫无心机地把自己的心思全盘托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有一件事想告知您——那就是,我爱您,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想从您那里取得任何好处,我——我只是想要告知您——我爱您!我愿意为您奉献一切!”
德米特里在弗拉基米尔心里的罪状除了愚蠢外又添上了另外一条:懦弱。这只小熊只敢借酒撒疯说出真心话。或许还能算上另一条,那就是不坦诚,明明迫切地期待着自己回馈他以同等的爱情,却只字不提。
归根结底还是不够信任,德米特里不敢确信弗拉基米尔也对他怀有相同的情感,所以才给自己留有余地。但是弗拉基米尔不喜欢这样,如果德米特里选择要爱他,那么他必须亲手斩断其他的退路,他必须卸下所有保护罩,冒着自尊被践踏、感情被伤害的风险,孤独地走向弗拉基米尔,那样他将不会失望于弗拉基米尔已经准备好的回馈。但如果德米特里无法全部做到,那么他什么都不会得到。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才是俄罗斯人该有的性格。
考验从此刻开始。
弗拉基米尔压制下怒意,轻笑着在他额头印下一吻,就像哄一个撒娇的孩子。
德米特里并不满足于此,双臂缠上弗拉基米尔的脖子,晕乎乎地仰视着他。弗拉基米尔锋利的眉骨下有一双精致狭长的蓝眼睛,被老鹰一般的目光盯着的感觉并不好受。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当作目标分析的德米特里压抑得发抖,他感到胸口一阵阵地发紧,整颗心扭在了一起。这一切反应都被弗拉基米尔尽收眼底,现在他几乎可以确认德米特里甚至比他预料的更为单纯,倒也正常,他完全具备一个天才学者所需要的所有品质,所有领域通用的绝佳悟性、专业上精深的造诣、旁人不可理解的固执和热情,以及对现实生活和人性的美好幻想。
救救我吧,德米特里在内心呐喊,他也不知道谁能在此刻拯救他,或许是上帝,死神也行。他快忍受不住这份煎熬了,被所爱之人以精确而锐利的目光注视,让他有种赤身裸体的耻辱感。弗拉基米尔好像把他当成了满口谎言的罪犯,用一把无形的尖刀缓缓切割他内心紧绷的一根精神的生命线。谁能来救救他,一秒钟的时间在他剧烈心跳的衬托下被拉长,体内涌动着一股怪异的电流,内脏仿佛化为一滩汩汩作响的水。或许他会离奇地死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原因,但一定是为爱而死,德米特里绝望地想。
他知道,现在,只要他后退一步拉开他与弗拉基米尔的距离,煎熬就会立刻结束,他酿成的错误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最多不过是被辞退,他还可以继续在圣大教书。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代价。真正的代价是他再也不会有机会进入弗拉基米尔的心。德米特里快要哭了,弗拉基米尔明明爱自己,却不轻易允许自己以爱回馈他。
夜风从没关紧的窗户吹进来,轻轻拂过德米特里发烫的脸颊,眼角浸出的泪珠沾在卷翘的睫毛上,“求求您,快告诉我,您也爱我——求求您!”德米特里啜泣着扑进弗拉基米尔怀里,不管不顾了,他决心要赢得弗拉基米尔的爱。如果弗拉基米尔不爱他,如果他的上司、法官、上帝,他的全部生活的审判者,决定抛弃他,他拥有的一切都像个残酷的笑话。弗拉基米尔没有立刻做出反应,这几乎给德米特里判定了无期徒刑。自暴自弃的想法充斥了他的大脑,大不了就死在这,死也不要当懦夫。
如果之前,德米特里还曾经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爱弗拉基米尔,还是说,只是一时的情绪,那么现在,在这段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德米特里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就像溺水的人渴求生命那样无可救药的渴望着来自弗拉基米尔的爱。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爱他都甘之如饴。就算弗拉基米尔打算整个摧毁他,把耻辱、恶意、肮脏的罪名全部施加在他身上,他都会甘之如饴,只要弗拉基米尔愿意爱他,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我爱您,求您了——请接受我的爱吧。”终于,德米特里鼓起勇气抬头正视弗拉基米尔的冷冽目光。他想,既然苏格拉底可以为了遵守雅典的法律而接受审判结果,那么德米特里也可以为了遵从内心的爱情而接受来自弗拉基米尔的任何惩罚。
“考验通过,我亲爱的季玛,”还没有听到期待中的那句话,德米特里依旧用那双噙满泪水的蓝眼睛看着他,接着,他收获了一个没有保留的热情拥抱,“是的,我爱你,季玛。我爱你——我当然爱你,很爱很爱——”带着温和笑意的尾音消散在空洞渺远的夜风中。德米特里心满意足地抱住爱人,小心翼翼地探出舌头舔舐对方的嘴唇,换来了爱人无数个更加热烈的带着血腥味和丝丝痛感的深吻。德米特里在接吻的间隙大口地吸入空气,幸福的烟火在他脑中接连不断地绽开。
德米特里轻快地笑着,高兴地挥舞双臂,“弗拉基米尔,你想成为伟大的领袖吗?就像你的名字一样,统治世界!”
“我从政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助别人。至于统治世界,季玛,我没有那样的野心,我只希望我能有价值地度过一生。”弗拉基米尔淡淡地说,月光照耀着他的金发。
电灯拉出他们纠缠在一起的影子,在苍白的墙壁上显得格外巨大,仿佛抬一根手指都能牵动世界的神经,但那时的德米特里沉浸在无边幸福中,他内心里只有一个直白的想法:自己终于赢得了弗拉基米尔的爱情。
潮湿灰暗的九十年代里,看一切都带着生锈的目光,有太多他未曾真切理解的东西。德米特里还需要三十年的时间去经历真实世界,才能明白,原来不是他赢得了爱情,而是爱情在与自我的持久对抗中永远获胜。
如今无论是自我还是爱情,都已经破碎得拼凑不出完整的理想。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经验都可以轻易得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长时间的相爱是一场溺水般的闷痛,是一条隐藏着肮脏、下流、无耻和失去自由的河水,什么都不会被改变,一切都在扮鬼脸。
快要到站了,他们不得不从回忆中抽身而出。德米特里在心里默默流泪,他们的爱情还安然存在着,他是在为他们的理想哀悼。
两人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痛苦,新年将至的热闹气氛并不能缓解盘踞在他们心头的焦虑感,只有沉默地坐在彼此身边时,听见对方的稳定的心跳声,才能获得片刻的安慰。
在寂静的车厢内,德米特里突兀地开口,“我们会一起获胜。”这是当年德米特里竞选总统时的口号,放在当下的语境里多了一份破釜沉舟的气势。
“是的,是的——”总统像一台生锈的机器那样僵硬地点点头,“我们不会把胜利让给任何人,我们不会。”重复了一遍当年德米特里说过的话,两人都放任自己的思绪沉溺在过去的温馨回忆中。
弗拉基米尔听懂了德米特里的忠诚。绝对的忠诚来源于爱,而绝对的爱使得忠诚毫无必要。在温暖的车厢内,在彼此身边,足够安全。看着德米特里的蓝色大眼睛里闪烁着温和跃动的光芒,他感到阳光照耀下柔柔融融的雪水流淌过心间,在这一刻他愿意相信全世界都为他们停驻,他们回到了春风得意的年代,美好的一切都静悄悄地不出声。
从车窗向外望,视野中是一片天光云影相交错的圣洁,而弗拉基米尔的灵魂是一团将要熄灭的烛火。
上帝啊,千万别让我失败,他无望地想,或者至少,别让季玛发现……
车厢外,雪花扑簌簌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