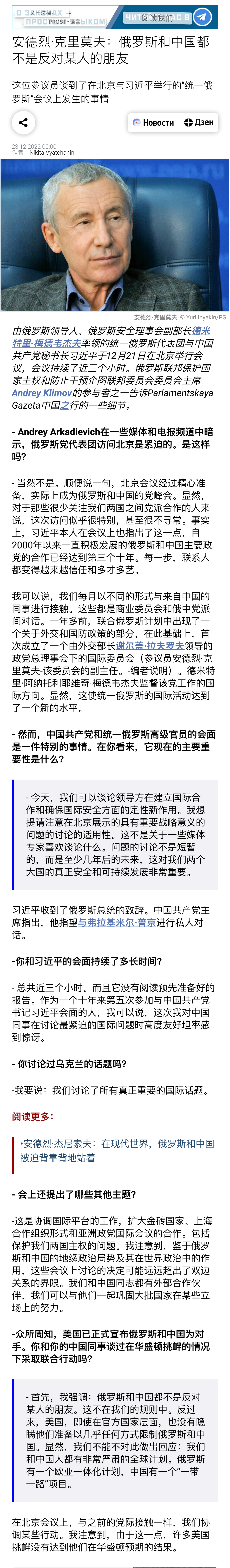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睡到自然醒。而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目前所拥有的,也正是这种幸福。
当然有些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自然醒,而是被吻醒的,但这不是更好吗?
“早安。”林间的晨光照进窗户,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从他的唇角边抬起头。
耳畔松涛阵阵,季玛陷在柔软的被窝里伸了个懒腰,眼睛睁开一条小缝,“我昨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到什么了?”瓦洛佳问。
“梦到一大波三体人攻打地球,然后白宫和五角大楼被摧毁,泽连斯基也被触手怪残忍地俘虏到了半人马座α星。”季玛的梦非常科幻。
“那你呢?”瓦洛佳失笑。
“我在阳台上吃烤肉庆祝,你给我烤的。”季玛嘿嘿笑,“可好吃了。”
瓦洛佳:……
“那咱们晚餐就吃烤肉。”所以说霸道总统先生对戈尔基九号的菜单真的是说一不二!
“……还是不要了。”季玛蔫蔫摊在床上,“咱俩这个月体检还没做呢,还是先吃清蒸海胆和野菜鱼汤吧。我就随口说说而已,你赶紧出发去开会吧,已经迟到了!”
瓦洛佳:……倒也不用如此尊重事实。
作为一个硬汉怎么能回回被保健医生训成三孙子,那样真是一点也不爷们儿。不过话虽然这么讲,但一想到烤肉,季玛还是忍不住深深叹了口气。
反正也醒了,他索性拿起手机开始网上冲浪。什么俄乌冲突,美欧头条,一看就特别适合自己现在的状态!
于是他拇指翻飞开始实名上网:
——如果该委员会成员真的想找出乌克兰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那么他们就应该停止像盲目的鼹鼠一样行事。
——仅2014年,在宣布脱离基辅罪恶政权独立的领土上,就有近2000人被杀,4000多名平民受伤。即使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受害者人数也有数十人。八年来,顿巴斯平民遭受大规模炮击,导致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亡。基辅暴徒杀害顿巴斯居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你必须完全失去良心才能看到这一点,并试图找到证据证明种族灭绝来自俄罗斯。
——愿他们受到诅咒,无论他们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资格,让他们在地狱里燃烧吧!
帖子发出去之后,果然瞬间就引来上万人评论点赞,大家纷纷表示骂得好爽,会说你就多说点。
季玛一条一条往下翻,点赞靠前的多是诸如“楼主应该去和老B登决斗!”“楼主你还是专心养鸭子吧!”“诚意出售破解版无人机,量大包邮,请点击链接——”此类不靠谱言论。
不过季玛显然不会被评论影响心情,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露出肚皮在私家森林里一边晒日光浴一边吃早餐更加舒爽了,更不用说还有香甜的牛奶椰子汁。
生活真美好!
但是,好纠结要不要戴墨镜。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先生很关心这个问题,全身皮肤都晒成了纯爷们儿的古铜色,单只留下眼眶周围一圈白,光是想想就很不鹰派。
吃完早午餐,季玛决定再写两篇帖子存在手机记事本里,以防吃饭时新想出来的骂人梗被浪费掉:
——遗传不良的半人动物
——发育中的、心智薄弱的生物,所有行为都纯粹是兽性
——那些亲属曾在党卫军服役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
——虚荣的白痴会集体尿湿裤子(和裙子)
——来自魔多、穿着绗缝夹克的半兽人
…… ……全部保存!!!
度过了繁忙的一天,处理了无数的文件,终于到了就寝时分。
“视频会上看你还在忙乎。”瓦洛佳躺在他身边,给他掖被角,“今天太阳不错,你得多晒晒,补钙。别老盯着手机,费眼睛。”顺手揉揉他的肚皮,软绵绵的手感特别好。
季玛趴上他胸口:“忙着怼人呢,好累。瓦洛佳,你不嫌我老发疯吗?”
瓦洛佳轻笑,伸手捏捏他的耳朵:“你呀,一辈子甭管哪个职位,总是这么认真干活儿,太敬业了我心疼。”
季玛一下子愣愣看着瓦洛佳,耳根忽然热了起来,气氛变得有些奇怪:“我,我早就辞职跑路了好吗!退休!退出核心决策圈的那种退休!”
看着他傻乎乎的神情,瓦洛佳低头吻了上去。
这这这是什么状况?!季玛吃惊万分,根本没想好怎么应对,连挣扎都忘了。
瓦洛佳眼里闪过笑意,又狠狠吮了一下唇瓣,才恋恋不舍放开,把人牢牢锁进自己怀里,“想给沙皇做个合格的圣愚,对不对?”
讨厌的克格勃!季玛顿时耳朵滚烫,把脸埋在他胸前。
头脑真是好聪明!
声音真是好性感!
瓦洛佳忍笑,把人从怀里拽出来继续亲,最后季玛稀里糊涂被放倒在床上。瓦洛佳加深这个温柔的亲吻:“我神圣的德米特里,我崇拜您……请赐予我您的神谕……”
昨天才……都这岁数了,又,又来啊……季玛晕晕乎乎,抱住了他的脖子:“我,我看到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还有盛大的烟火,就,就在不远的未来……”
注:圣愚,又称颠僧、佯狂者,是俄罗斯东正教特有人物。他们通常是浑身污垢,半疯半裸体的游民。他们中有些人几乎不能言语,所发出的声音却被解释成神谕。被认为是上帝赐予人间帝王的礼物。
据说这个词产生于十一世纪基辅罗斯时代,盛行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它来源于东方的萨满教,但俄国和西方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则认为它来源于拜占庭的愚人传统,随东正教的传入而产生。
圣愚一般行为怪诞,有点像竹林七贤或是活佛济公。但不同的是,圣愚出身背景迥异且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通常蓬头垢面、愚痴癫狂,有的甚至半裸身体,脚套镣铐。他们时而给人治病消灾、占卜祷告,时而诅咒下蛊、坑蒙拐骗。他们游弋在城乡,也栖身于宫廷,成为平民与贵胄的座上宾。圣愚被认为是上帝的使者,曾受到历代沙皇的重视。从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都对圣愚推崇备至。莫斯科红场著名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就是伊凡雷帝为纪念圣瓦西里而命名。瓦西里被当时的俄国人奉为守护圣人,常常赤身行走,忠诚于基督与国家,曾反击鞑靼人的袭击,拯救了莫斯科,死后伊凡雷帝亲自扶灵,封其为圣徒。而俄国历史中普遍被认为是最近的一位圣愚就是妖僧拉斯普钦,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不仅相信他能用祈祷治疗皇太子的血友病,而且对他无比信任言听计从,不仅请到宫中议政,甚至在外征战时也会因为他的信件而改变战争计划。
圣愚这种现象也反映在俄罗斯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里,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在俄罗斯民众的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的特性:专制与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的恣意妄为;残酷的暴力倾向和善良敏感的人性;崇奉礼仪和追求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自我吹嘘的民族主义和普济全人类的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流于表面的虔诚;深厚的神学土壤和战斗的无神论视角;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俄国作家什梅廖夫认为,俄国人喜欢走极端,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而圣愚或许就是能把表面上完全不能调和的品格统一在一起的东西,是有可能更好团结各方向选民的有力手段。